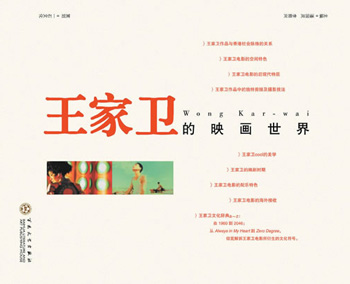
《王家卫的映画世界》
潘国灵 李照兴 主编
一石文化 策划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5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由多位香港资深和新晋的影评人、文化评论人编写,是目前惟一以香港观点出发的王家卫评论专集,是认识王家卫作品、了解香港电影文化的必读书。
全书从三个不同角度分析王家卫作品的文化性与艺术性。
评评理:畅谈贯穿王家卫电影中的题旨、风格特色等。如:王家卫作品有何90年代香港文化特色;何谓王家卫美学风格;从《旺角卡门》到《2046》八部作品的个别详细评论。
谈谈戏:是资料性的参照、补遗,让读者更立体地理解王家卫的创作及其成功的背景。如:记述王家卫的电影在海外逐渐受礼遇的进程;细数王家卫编剧时代的作品,提供阅读王家卫日后导演作品的背景基础。
面对面:张叔平、杜可风为你揭开与王家卫这最佳拍档的漫长合作之道;潘迪华解释王家卫的上海根;刘镇伟剖白跟王家卫的手足深情;谭家明、梁朝伟追述《阿飞正传》那已成传奇的最后一镜。
目录
简体字版序 过去与记忆 潘国灵 4
序一 为何要一本王家卫专论? 潘国灵 6
序二 诠释与过度诠释 李照兴 14
王家卫简介 16
1 评评理
横移综论
王家卫电影的记忆与遗忘 朗天 22
王家卫电影中的空间 也斯 33
王家卫的后现代城市超级市场 张志伟 46
80年代的60年代文化想像——又或是《阿飞正传》的记忆外延策略 汤祯兆 59
舞动的影像风格——《阿飞正传》的镜头赏析 何思颖 65
王家卫cool的美学 李照兴 81
大写特写
《旺角卡门》——铁汉与柔情,江湖与爱情 刘钦 104
媚行性感的《阿飞正传》 罗维明 111
《重庆森林》的场域游移与数字恋爱 家明 113
《东邪西毒》——时间的灰烬,沉溺的极致 潘国灵 121
《堕落天使》——告别江湖,轻装上路 黄志辉 129
《春光乍泄》——王家卫来来去去只说一个故事 清心 138
如花美眷——论《花样年华》的年代记忆与恋物情结 洛枫 145
《2046》戛纳版与公映版——立此存照 李焯桃 157
《2046》——爱情和时间的永远轮回 张凤麟 166
主观镜头
反得奇,望得怪——《东邪西毒》剪接的两点观察 何思颖 174
《春光乍泄》——揽着自己,独跳探戈 陈嘉铭 185
发花癫 林奕华 195
过场 I:地理志(香港、台湾) 214
2 谈谈戏
越剧钩沉——王家卫的梦呓 迈克 226
编剧时期的王家卫 蒲锋 233
王家卫电影音乐图鉴 罗展凤 239
王家卫电影的海外接收 李焯桃 259
《2046》,5 years in the making 魏绍恩 268
过场 II:地理志(海外) 280
3 面对面
王家卫现身说法 Laurent Tirard 289
即兴美指遇上即兴导演——专访张叔平 潘国灵、刘 293
杜可风访问札记 李安 303
你可以说我是完美主义者——专访谭家明 潘国灵、李照兴 309
若两者可结合,还不是天下无敌?——专访刘镇伟 登徒 315
到底是上海女人——专访潘迪华 卢燕珊 323
那时我好大压力!——专访梁朝伟 登徒 331
王家卫文化词典a—z 潘国灵、李照兴 333
王家卫作品简介 341
作者简介 347
鸣谢 350
内容选刊:
诠释与过度诠释
李照兴
1
为什么编一本王家卫的评论书?在尝试反映、诠释一位导演的作为之外,我想当中还有点私心,观众的私心。
做评论可以是为导演定位,但反过来也是为了明了自身。
问为什么是王家卫,也等如问:从阅读、挪用王家卫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什么?
于是,出现于本书的文章,也就是一趟各自演述看戏的观点、关注、视野与兴趣。
如果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如何透过观察与归类、思考,尝试去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为世界建构意义),评论人的责任,大抵就是为电影建构意义;而去到终点,其实也就是为自己作为观众,缔造意义——为自己建构意义。
即是说:如何解释观众对电影的热爱和热恨。
这可归结为三种阅读电影的方向:
一、评价电影的技术与风格本身——是对电影作为艺术品的审美、阅读;
二、意识形态批判——讨论作品的内容信息于社会发放的作用,或其产生的社会条件;
三、晚近的评论方向,朝着探求作品跟读者/观众的互动,或曰:观众如何借文本产生一种属于自己的意义与乐趣——文本的快感。
2
这三种阅读方向,在本书中都分别呈现。当然,三种方向未必分得一清二楚,甚者是相互夹杂。
例如书中对王家卫镜头或剪接技巧的分析,笼统可归作第一类。何思颖便在《舞动的影像风格——〈阿飞正传〉的镜头赏析》和《反得奇,望得怪——〈东邪西毒〉剪接的两点观察》两文以电影分镜详细集中讨论《阿飞正传》和《东邪西毒》的技术特色,指出多重移动长拍镜头(multiple movement long-take)在前者的圆熟应用,以及后者借非传统的不对位剪接或如双人镜头(two-shot) 的镜头运用,令观众一新耳目,并指出那也可能是一般观众觉得该片难明的原因之一,即为替电影making sense的好例子。
另方面,朗天对王家卫电影所出现的时代背景(主要为90年代)做出探讨,延续他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时政观察,指出王家卫作品中的共通母题,如忘记、寻找、身份等,实为香港后过渡期的产物;又或者陈嘉铭在讨论《春光乍泄》时所抱的政治正确观点,批评该片在处理同性恋上的异性恋化处理,则是典型的有关电影作品意识形态的分析。
而评述落到迈克之手,又已经发展至另一阶段。他把王家卫电影如《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中若有若无的越剧元素众里寻他,思疑王作品中的潜在氛围(跟王的上海人身份有关),指出电影中个别场面的处境或气氛跟几套越剧的情节近似,就正是作者自身的刻意诠释。洋洋洒洒在种种嫌疑迹象中荡漾自寻乐趣。未尝不是文本快感的高潮。
3
但王家卫真是这样想吗?如迈克的提问:王家卫梦中可听着越剧吗?
我们常常都听到这种批评:那不过是你们评论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导演或编剧可没承认过有此本意呢!
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解读过程。
其一是,特别针对富作者风格的导演而言,在其贯穿的系列作品中,实在有太多相关文本元素,可作归纳统一分析,而这种共通,也实在不可能看不到,也没可能是巧合。例如王家卫多部作品中均出现的角色形态,他们的漂泊身份、缺少家人、割裂的世界、自言自语的个性等。做评论,正是以一种关注与洞悉的敏感眼光,找出一点作者或彰显或潜在的意图。
作品当然有自我的发声,不需要靠别人指指点点代其传译。但有趣的作品往往却模棱两可、暧昧不明,不止拥有单一种霸道性的诠释角度(如视作者的原本意图即为其最决定性的信息)。从多重肌理的文本matrix中找出不同的诠释角度(好的作品往往都具大程度的可供诠释性),享受寻找与诠释的过程,也就是诠释之道。此所以汤祯兆会在《阿飞正传》的探讨中看到我们80年代人的记忆;潘国灵会断言《东邪西毒》是王家卫再见理想之作。积极主动的诠释者/评论者为电影与它产生其中的社会氛围串联起一定的关系。Making sense的对象,是电影,是世界。
其二是,评论的另种乐趣在于评论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今次评论人真可以自说自话(像一个王家卫角色),阐述一种过度诠释,今次making sense的对象,是自己。你总得解释你为何会为电影中的某个镜头某种格调如此执迷。
4
极端例子:
迈克在《越剧钩沉——王家卫的梦呓》中的疑问,不是很多人懂得问的题目。我完全未听过他文中提及的越剧(除了在《花样年华》出现过的点点),而这越剧迷却大胆假设:这深植于上海文化的气息,王家卫可有感染?文章作者把自身关心的题目投射进被诠释的作品中,表面上诉说越剧与王作品的眉来眼去,实际像打开电视看王家卫却让它无声,音箱反而播着越剧折子戏。
这里,最重要的是:王家卫心中究竟有没有越剧其实已无关宏旨,最重要是论者已哼在嘴边潇潇洒洒。
又或者罗维明“阿飞写阿飞”,由60年代数落至2003年4月1日“哥哥”(张国荣)的“飞”,两个年代的印证,电影与明星的传奇交融,观众又如何把《阿飞正传》的文本与对白据为己有(他引的那句友侪间传颂的“喝了,好过睡了”的对白,大抵笔下所说的友侪也就包括我),怕就是王家卫电影作为cult film的最佳例证。
5
罗兰·巴特在《 S/Z》一书把文本简略分为两种,一种是供阅读的文本,另一种是供书写的文本。前者近于古典的文本,诠释空间窄小,作者意图明确,读者介入程度低。后者就如一个可供读者高程度介入,进行重新创作的开放文本,作者就像在原有的文本上再自行书写,得出另一层属于读者创造的文本意义。
6
(不要介意到这里才实际介绍本书的环节划分)本书分为三个大部分及三个小部分,前者包括评(评评理)、述(谈谈戏)及访(面对面),而三个小部分则由两段地理志及王家卫文化词典构成。
不同的切入角度大致也道出了普罗观众在观看王家卫作品时的落点:
评是从文本出发,可以是替作品解画,也不妨用理论去阐明观点;述是借题发挥,为王的作品特色提供更丰富的背景资料及文本乐趣。至于访,就很有种各砌拼图,从各异的口述重组王家卫作品的各种意象。
而词典与地点已经是观众看完电影后再加诸的自行创作,把电影文本活化,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记得的声音,向情人说的对白,与恋人走过的街角。
7
评是一种解画,也可以是另一种批判,例如:
何思颖解拆镜头和剪接的非典型运用之同时,指出这独特手法强化了王家卫作品中“见与不见、见而不视、视而不见”的处境。
汤祯兆其实已经在写80年代的香港史。
而我终于想出人们热爱王家卫电影的原因,可以无关故事,而只因角色相当有型,对白入心。
当然不得不提林奕华,他提出的问题依然惹人反思:“我们对自己喜欢和接受的东西,到底有几认识?有几清醒?”
8
述是资料性的参照、补遗,让我们更立体地去看王家卫创作及成功的背景,例如:
李焯桃以多年参与国际级电影节的经验,亲眼目睹王家卫在海外逐渐受礼遇的进程,详细记述了外国评论界、学者及电影节圈子对王的接收,在一定程度上把王家卫神话置放于一个脉络当中。
蒲锋细数王家卫编剧时代的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一个阅读王日后作品的背景基础。
9
不过对稿时看得人大笑或啧啧称奇的,总是访问。
有不少像“罗生门”,小部分不为人知,而更多是第一手的记忆、感想、意见,助我们更立体地认识王家卫电影的幕后世界。
例如潘迪华以自身经验出发,指出香港小上海社区的特色,如何在王的作品中埋下种子,就是妙绝的个人感怀,同时映照那个年代的香港风情;梁朝伟首次公开他拍《阿飞正传》的详细过程等。
藏在墨镜后的导演,始终有他的多种面相。
10
词典内a至z,已经是轻舟过后的絮语片断。是对曾喜欢过的曾被打动过的一景一物书本人情的纪念册。由1960数到2046;从Always in My Heart一直到zero degree。像完场前快速flash back(闪回)的画面。
编辑过程中,我们已尽量平衡包容各主要而重要的观点,可遗憾不是没有,如浪人的题旨、演员的运用等角度,均未能找到适合的文章详释。此外,由于2003年下半年正值王家卫忙于拍摄的紧张日子(其间他在拍摄两部作品,包括《2046》及Eros,又监制《地下铁》),以至未能抽空接受访问,肯定是本书的极大遗憾。但作为一本以香港评论人出发,谈一位当前重要的香港导演的专书,香港评论人观点得以抒发结集,这已是一个重要起步。
11
当然得特别鸣谢王家卫与泽东电影公司的同事在各种安排及相片授权上的通力合作;庄澄与寰亚公司的相片授权;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是黄爱玲的全力协助;香港三联书店资深编辑李安在策划、联络及编务上的悉心打点;众位受访者的坦诚交心;以及各非本会会员,包括小草、家明、洛枫、迈克、卢燕珊及张志伟的慷慨赐稿。当然也少不了陈一峰、梁广福、Seeman的摄影,黄志辉的美术——齐心合力做点事出来,就是最开心的。
李照兴:文化评论人、作家及出版人,曾任编辑、记者、电台节目主持人,专注书写各类流行文化观察,文章见于香港《明报》、《经济日报》、《号外》;内地《21世纪环球报道》、《南方都市报》、《城市画报》及台湾的《电影欣赏》、《诚品好读》等。亦于各院校筹办及教授多个电影/流行文化相关课程。作品包括《男人那东西》、小说《香港酷酷》、评论集《香港后摩登》;主编《香港101》、《裙情汹涌》、《经典200——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上海101:寻找上海的101个理由》及《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等。
舞动的影像风格——《阿飞正传》的镜头赏析
何思颖
1960年某月某日,刘德华演的警察与张曼玉演的苏丽珍一起度过了午夜前的一分钟。[1]
如假包换的一分钟。因为那场戏是用一个连续不断的单镜拍的。那个镜头,刚好也一分钟。
大家都知道时间是王家卫电影中十分重要的议题。在《阿飞正传》里,张国荣演的旭仔与苏丽珍订情的绝桥是引诱她一同度过“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前那一分钟”。[2]她与警察一共有三次见面机会,是她逐渐消除对旭仔情意的过程。最后一个晚上,她情不自禁地回到旧地,穿着订情之日那条裙子,抽着旭仔爱抽的烟。午夜前一分钟,警察忍不住严厉地教训了她一顿。王家卫含蓄地(也许不自觉地)用了一个刚刚一分钟的单镜,来表达这一段情的完结。[3]
这一分钟是电影的转捩点。时间上,这场差不多正好在影片中间点的戏[4],不但代表了苏与旭仔的完结,亦开始了她与警察之间似有若无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故事从这里开始自旭仔与两名女子的感情纠缠扩展至较宽阔的叙事范畴。难怪这一分钟的完结,是如此非典型王家卫地充满戏剧性:一扇急剧横扫的黑门、被铁门由半掩至完全遮盖的大钟、突然响起而又震耳欲聋的钟声。
这个刚好一分钟的镜头,王家卫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拍法,当中包括了各种不同的角色走位、摄影机运动、对焦控制及画面构图,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效果。
演员、摄影机与镜头的群舞
王家卫最杰出的成就,是“实践了所有香港电影在艺术方面努力的梦想:在形式上作无限自由的实验之同时,又反映着各种情爱关系的哀伤喜乐。”[5]各种风格的实验,并非炫耀自我的show quali,而是紧扣内容的展现,匠心别具地表达了电影的意念。他的情节无论如何沉重,情感无论多么苍凉,作品总有一股形式上的快感,“那份拍电影的愉悦、率性与自由”[6],令观众与导演一同乐在其中。《阿飞正传》是王家卫成熟之作,多种技巧上的突破,其后在其他作品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应用,而且经常表达了不同的意义。本文特别讨论电影中两种风格方式。
其一是上文提及的一分钟所用的单镜,可称之为“多重移动长拍镜头”(multiple movement long-take)。为免累赘,姑且简称之为“MuMo长拍镜头”。
MuMo长拍镜头并非王家卫首创,历来很多导演都喜欢采用,著名的有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及匈牙利的扬索(Miklos Jancso)。安氏与扬氏的长拍充满史诗情怀,王家卫则专注格局较小的儿女私情。王氏特别之处,是他的长拍经常都有大量的焦点变动。
在《阿飞正传》那个一分钟的单镜内,警察与苏丽珍有一段颇长的对话。王家卫的角色是自闭的,要不沉默寡言,要不自言自语。《阿飞正传》中交谈场面要比他以后的作品多,每次都在颇为重要的时刻。镜头以警察背向摄影机而面对苏丽珍的中景(medium shot)开始,其后两人像置身歌舞剧一样,展开了两次“你追我赶”的舞步,转身、扭腰、转面,其间彼此又改变位置,一时她向着镜头,一时他对着摄影机。最后,他对着背向我们的她说:“做人……要么要,要么就不要……不然,从这分钟起……”她猛地扭转身,将画面变成一个两人同向的特写,近乎歇斯底里地说:“你别提这分钟!”而在这一分钟刚要完的时刻,大钟“当”地响了一声(图1—8)。
两人的走位,摄影机以准确的运动捕捉了,并不断或轻微或剧烈地变焦,将我们的注意力不停地转移着。效果恍如一场舞,一场刘德华、张曼玉、摄影机与镜头(此处指lens)互相配合的群舞。
正如出色的歌舞片,警察与苏丽珍不停转换的位置,代表了彼此的心境及关系。王家卫的角色交谈时,往往都目不相接,你低头时我远望,我凝视时你闭眸。他们的身体也貌不合神亦离地对着不同的方向,以构图表达他们的隔膜。就这样,警察与苏丽珍跳了整分钟的舞。
王家卫的角色也经常采用身躯与头部不协调的身体语言。他们摆着各种扭曲的姿势,坐向东时头面北,站往西时脸朝南。一方面反映了角色间的疏离,同时更表达了他们身心挣扎、灵欲相持的状态及保护自己与付出自己之间的矛盾。
在那午夜前一分钟的“舞蹈”中,警察腰板挺直地训话,他的眼神虽然隐藏在警帽底下,锐利的目光仿佛仍透过帽舌直射向苏丽珍。她却不断回避他的凝视,并且经常或转身或“头身不调”地抗拒着他的关心。
他与她,也不断笼罩在各种灯光环境中,身体往往被暗影覆盖,只有局部照明。这一来营造了优美的影像效果及表达了角色的矛盾,亦是贯彻全片的光暗母题的展现。
值得留意的,是午夜后的一场戏,也刚好一分钟,虽然王家卫一共用了三个镜头。第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大钟特写(图9)。第二个是短促的远景,让我们看到继续关闭的铁门及旁边还折着的铁闸(图10)。第三个是55秒的特写,苏丽珍在张开了的铁闸后平静地宣布:“望着这个钟,我告诉自己,我要由这一分钟开始,忘掉这个人。”在她背后,警察默默地站着,虽然因为离开了景深而显得模糊,却与她面向同一方向(图11)。同样重要的,在这个55秒的单镜内,我们开始听到背后不知从哪里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声。
王家卫的MuMo长拍镜头是配合了各种电影元素来表达故事意念的技法(变焦的应用稍后再讨论)。这种配合需要精密的设计及多方面的协调,对演员及摄影师的要求尤其高。这也是他的电影经常超资过时的原因之一。
除了午夜前的一分钟,《阿飞正传》还有多次重要的戏剧时刻沿用了MuMo长拍镜头,例如苏丽珍与旭仔分手的场面、菲律宾唐人街客栈内旭仔与当了海员的警察的对话及旭仔在电影内第三次去南华会,要求苏丽珍与他一同看表那个同样刚好一分钟的镜头。而王家卫出色之处,是他风格上兼容并包的直觉。他不是安哲罗普洛斯或台湾的侯孝贤,不会坚持长拍。他会视情况而定,适时地打断MuMo长拍镜头,插入其他单镜来达到更有力的效果。例如客栈内的交谈(图12),长拍镜头突然中断,接到旭仔一个中景,心不在焉或有意无意地问:“现在几点?”(图13)警察回答(“三点半”)时,又回到了刚才那个长拍镜头(图14)。
多重移动的手法也不限于长拍,而是经常以不同长度及方式(走位配变焦、人与机互动、机动焦也动)在其他场合中出现。
景深的运用
王家卫的世界是疏离的。他的角色,经常都是执迷不悟、自恋成狂、孤独寂寞的人。他们彼此隔绝,与环境却有份若即若离的痴缠关系。《阿飞正传》的地域观念虽然没有其他王家卫作品那么强,时代氛围(留意,不是历史)的重现及细心得有点恋物(fetishistic)意味的布景与道具,却为电影炮制了一股浓烈的环境气息,有点像张爱玲谈中国旧文学:“细节引人入胜,而主题永远悲观。”[7]
角色与角色及环境间的微妙关系,王家卫巧妙地以景深(depth of field)的处理来表达。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会以深焦、浅焦及变焦等方式来赋予不同的意义或感觉,营造了丰富的视觉魅力,亦含蓄地润饰了角色状态及故事处境。
前面提到《阿飞正传》的MuMo长拍镜头像一场群舞。其实这比喻可以引申至整部电影。王家卫的艺术感
人之处,是在即兴与刻意之间保持了平衡。这也是直觉与计算之间的平衡。拍戏不用剧本的神话,需要的是繁复的排练过程及鉴别演员特质的慧眼。王家卫拍《阿飞正传》,大胆地起用了大量极端浅焦的场面,成功地表现了角色的封闭及他们之间的隔膜,同时亦凸显了演员的个人特质。在适当的时机,他会变动焦点来捕捉角色的神髓或转变中的处境。电影就像一出百老汇歌舞剧,演员、摄影机与镜头焦点彼此配合地婆娑起舞,制造出美妙的影像效果。
在这种视觉策略下,角色与角色及环境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非常有趣的效果。他们就算近在咫尺,看上去却觉得中间隔着浩瀚的鸿沟。另一方面,两个人被狭窄的景深硬生生地分开了,但焦点以外模糊的身影又让我们感染到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怀,真可谓“焦断情连”。王家卫的好,是他即兴与刻意、直觉与计算的创作方式,可同时产生多种意义。
王家卫的景深处理,将画面变成一个多层面的立体空间。摄影指导杜可风的摄影机及镜头(这里指lens)在王家卫精心设计的安排下,不断在这空间里搜寻适当的焦点。在不同的时刻,个别角色的心理或角色之间的关系会有不同的状态,而镜头焦点则在画面上为这些状态做出影像化的演绎。
景深的处理包括前景与后景的互动。有时这只是简单的过肩镜头(over-the-shoulder shot):两个角色同时入镜,一人肩背在焦点以外,另一人侧面向镜头而对准了焦。例如上文讨论的一分钟单镜,警察教训苏丽珍时便是面对背向镜头的苏。后者乌黑的头发在前景的焦点以外摆动,在银幕左方边缘进出画面。这个构图是电影开始时旭仔到南华会泡苏丽珍时一个镜头的翻版,而她除了穿了同一条裙子外,头上也同样戴了一个银亮的发夹,同样在模糊中闪耀着淡淡的光。前景的她与后景的他,两场戏都同时有吸引与抗拒的意味,但刚开场的吸引与抗拒,与故事发展到一半的吸引与抗拒则有很大差别。差不多的构图,同样的前后景互动,产生了暧昧的前后呼应。
前景与后景的互动还有其他较复杂的形态,通常是一名角色在近镜前方,另一名角色在远镜后方,两人则像跳舞般转移位置,借彼此的距离及与环境的关系表达变动中的状况。在《阿飞正传》中,这种调度方式虽有时在深焦中进行,但大部分都出现于浅焦情况中。
例如刘嘉玲饰的咪咪到南华会找苏丽珍那场戏,最后一个镜头是咪咪的高角度大特写。苏在她身旁蹲在地上,离开了镜头焦点(图15)。刚哭过的咪咪,“跌落地还抓把沙”(硬撑)地试图以伤害他人为自己重拾尊严:“讲到底,他都是因为我不要你的。”她边说,摄影机边慢慢地往右摇,为即将回应的苏丽珍预备空间,并且在话说完后顺势将焦点转到苏的脸上(图16)。她从容地起立,站在焦点以外的咪咪旁平静地说:“现在哭的是你,不是我。我已经没事好久了。”(图17)说完后转身走出画面外,摄影机则朝反方向摇,并又顺势变焦,让我们感受咪咪的哀伤及见证她活该受的侮辱(图18)。
另一个例子是咪咪回到更衣室的一个MuMo长拍镜头。她背着镜头向着Art Deco图案的门走(图19),手提式稳定型摄影机在后追赶。她慢下来开门,摄影机追上了,越过她的肩膊看到坐在更衣室内,但焦点以外的张学友。镜头缓缓变焦,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及墙上围着灯泡的化妆镜及堆陈在桌上的瓶儿罐儿(图20)。张转过头,深情地看着焦点以外的咪咪。她失望地转过头,摄影机也随着变焦的时刻往前推了一推,使画面成为她的大特写,并把张摒弃于焦点以外的背景中(图21)。她大剌剌地说:“你吗?我还以为是旭仔。”张站起身走近,她稍转头过去相迎,摄影机又顺势推前及变焦到他身上并把镜头转为中景(图22)。“他去了菲律宾!”他说完后焦点又回到她的侧面特写(图23)。她毫不在乎地绕过他往里走,从特写走到中景,焦点亦随着她转向室内,与她一同在镜前停下(图24)。张回转身望她,并向旁边走了几步,让两人的倒影都在镜中出现,将画面从双人镜头(two-shot)转为四人镜头(four-shot)(图25)。两个人及两个倒影默然地站着,她突然把桌上的瓶瓶罐罐狂扫到地上,并捧起一个大型玻璃烟灰缸,奋力掷向镜子(图26)。
前后景的互动,配合了角色的走位及摄影机的运动及镜头焦点的更换,制造了不断改变的影像,表达了转换中的心理状况及角色关系。
在更衣室的单镜中,景深的处理已包括了环境的形态。前景与后景的策略,亦可应用于人与环境上,虽然变焦的程度会比较轻微。苏丽珍与旭仔分手时,她在大特写中毅然宣布“我以后不会再回来”后走出了镜头,她稍微曝光不足的脸离开后,留下一面曝光过强的墙,在空洞的房间内照耀着专心对镜梳头的旭仔(图27—28)。
另一个前后景互动的人与环境的例子却是一个没有变焦的镜头。那是结尾时梁朝伟独自准备出门的单镜。无名的男子跷着腿或躬着身修甲、梳头、穿衣,房间与他有一种特殊关系。超低的楼顶,过分曝光的灯泡,挂满衣服的墙,晒着太阳的藤椅,放着烟、钱与纸牌的桌面……王家卫的摄影机左摇右摆地追随男子,前景与后景间有一种诡秘的感觉。再加上一反惯例地采用了广角镜,与电影其他大量浅焦镜头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令这场戏更添神秘莫测的味道。
母题强于主题,情调胜于情节
《阿飞正传》是王家卫风格确立之作。他本着香港本色,把一些现成的电影技巧,融会贯通成为极端个人的艺术言语。这些现成的技巧有新有旧,新的例如:几乎成为王氏品牌的停格加印、MTV式剪接及剧烈的摇镜等。旧的则包括:省略式的叙事体及剪接、上文讨论的景深运用及多重移动的配合等,都是颇为基本的电影语言词汇。王家卫将这些或新或旧的现成材料“炒成一碟”,在合成的过程中赋予新意,发展出独特而迷人的风格。
王家卫的电影故事性颇薄弱,但仍有很感人的力量,既有个人情怀,亦有深沉感触,更有历史感伤,很多人都讨论过他作品中的“九七”回归情结。美国学者大卫·波德威尔(David Bordwell)在其 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香港电影王国》)一书中指出,王家卫其实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浪漫主义者。[8]其实他作品内的题旨,往往有故作深刻但又欲言又止,结果词不达意之弊,尤其是最具野心但结果充满感情自渎意味的《东邪西毒》。无论如何,他仍能以灿烂醉人的技法,表达其丰富的感情,观众亦往往被深深地打动。
此所以王家卫作品经常是母题比主题强,观念如时间、地域、记忆、缘分等比刻意的“雀仔(鸟儿)没有脚,只可以飞呀飞”或“被人拒绝和怕被人拒绝”[9]来得真切、隽永。我们不一定记得或同意他各种课题,但我们不会忘记他电影内的哀怨、苍凉及无奈。景深的运用与多重移动的配合等技法,是王家卫捕捉澎湃感情的基本工具。他是感性强于理性、情调胜于情节的导演。
他那合成现有材料而别树一格的电影语言,必须获得成熟的技术支援。《阿飞正传》中景深的精彩运用及演员与摄影机的紧密配合,是港产片个人艺术与工业体制彼此配合的成果。今日回看,《阿飞正传》1990年12月的面世,是香港电影个人艺术视野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主流工业开始衰退的先兆。今时今日,艺术电影已成为香港电影的救赎,王家卫更成为世界各大电影节竞相争取的国际名牌。香港电影界各大哥大姐级明星不惜暂停挣快钱,而陪他长期作战,技术人员也迫不及待为他效劳。他的预算经常都包括外国资金,但他的作品仍然是不折不扣的道地香港艺术。
作为“迟来的新浪潮”导演[10],王家卫成就了当年新浪潮达不到,甚至想也想不到的任务,将港产片像法国或德国新浪潮一样,带进了电影艺术的殿堂,尽管他曾说自己只是个“不很成功的商业导演”。[11]
《阿飞正传》创立的风格,其后在王家卫的作品中不断演变。前景与后景互动的景深运用,在《重庆森林》中与停格加印的技巧合成,发展出脍炙人口的效果。梁朝伟饰的警员靠在速食店后景慢条斯理地啜着黑咖啡而前景的人群浩浩荡荡地疾飘而过的效果,震动了全世界,从此成为他的招牌影像。到了《堕落天使》,超广角镜头排除了浅焦的应用及削弱了疏离感觉,而长拍镜头因为不能使用变焦而限于摇镜及摄影机的跟进,角色间的关系好像拉近了。但是,被广角镜头夸张了的样貌及身形,一方面加重了角色的扭曲状态,另一方面亦强调了他们孤芳自赏与寂寞封闭的可怜。
从变焦到停格加印到超广角镜头,王家卫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那丰富澎湃的感情无论如何沉重,表现的手法却永远透着一股焕发的乐趣,一种形式主义的热情。王家卫不是为风格而风格的导演,但风格却是他的艺术魅力所在。
【注】
[1] 王家卫喜欢玩弄时间,有时好像很准确,有时又故作含糊。我们只知道这一刻是在1960年4月16日与1961年4月12日之间。较早前,苏问旭仔他们认识了多久,他也含糊地答:“好久了!” 此外,这一分钟不一定是刚刚午夜前一分钟,而有可能只是午夜前某分钟。
[2] 有趣的是,这一分钟在银幕上反而只有15秒。
[3] 严格上应该是四次,但头两次在同一夜发生,而我们知道三次是因为苏的衣服。王家卫喜欢以省略式叙事与观众玩游戏,类似的情况是王菲在《重庆森林》中抹窗一段,也只有从衣服上可看出时日已变。
[4] 这场戏在电影的43分钟完结,而全片是92分钟,但如不算梁朝伟最后一段,则只有89分钟(以上时间根据电影 DVD 版本)。
[5] 罗维明,《飘忽城市心事》,《1994年香港电影回顾》(香港电影评论学会,1996),页69—70。
[6] 黄爱玲,《人影幢幢的森林》,同上,页62。
[7] 张爱玲,《余韵》(台北:皇冠出版社,1987),页21。
[8] David Bordwell, 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80-281.
[9] 杨慧兰、刘慈匀,《长剑轻弹漫说江湖事》,《电影双周刊》1994年9月8日,页41。
[10] 李照兴形容《旺角卡门》为“迟来的新浪潮电影”。参看李照兴,《香港后摩登》(香港:指南针出版集团, 2002),页114。
[11] 引述自Fredric Dannen & Barry Long, Hong Kong Babylon: An Insider阵 Guide to the Hollywood of the East (New York: Hyperion, 1997), p.52。
何思颖:返于香港及美国休斯敦的作家。曾任多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英文编辑。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电影课程,并为香港电影资料馆特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