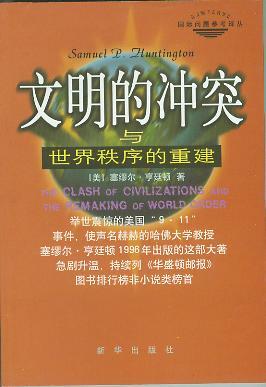
“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印证了亨廷顿在卡特时期预测的正确性;同时,也为美国提出了一个课题:冷战之后,“我们”将如何行动?
1992年,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胜利,这将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形态。亨廷顿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在1993年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后来他说,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我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以此为基础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将转变为不同文明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而三大文明交界的“断层”地带最有可能引发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张立平研究员当时是这本书的翻译。据她介绍,当时最让她头疼的翻译问题就是“断层”一词。“断层,英文中是frontline,指的是不同文明的交界地带。中文很难找到这样的词。最后经过反复斟酌,用了‘断层’一词。”
亨廷顿在9-11后多次声明,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并非文明冲突,更不是“十字军东征”。然而,《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清清楚楚写着:“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
这或许反映了他本人的矛盾心态。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教授回忆,亨廷顿在1998年曾和他有过一次长谈。“他坦诚地承认他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担忧才是最深切的,他自己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希望美国到处插手他国事务的扩张主义者。”
在亨廷顿离世时,巴以之间再次爆发冲突,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这是否是“文明的冲突”的一个诠释?不过,“文明的冲突”又是否只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真正的遗产
2004年,亨廷顿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在书中,他表达了对美国文明衰落的担忧——由于日渐增长的非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公民的增长,美国文明赖以立身的自由民主价值可能“迷失”;美国的“民族大熔炉”也许会蜕变成“民族大沙拉”。
这本书引起的争议不亚于《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因为这本书被很多人贴上了“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亨廷顿的离世,也将争议留给了众人。
在采访中,受访专家几乎一致表示,他们更喜欢亨廷顿的另一本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文明的冲突》与《第三波》等著作的“光芒”遮掩下,这本书似乎稍显黯淡。不过,思想史反复证明,传世经典往往与流行与否并无太大关联。
1968年,在越南战争激战正酣时,亨廷顿完成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书中,亨廷顿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的两种政治变化路径:权威政体压制平等与民意表达,导致民众反抗,最后走向崩溃;民主政体过度奉行民粹主义,导致秩序丧失,最后走向崩溃。这似乎是一个两难困境:无论权威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发展中国家都无法顺利实现现代化。
亨廷顿对这个两难困境的回答是这样的: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而实现“均富”能够消解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这样,现代化就能够平稳实现。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年4月1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
●16岁时考入耶鲁大学,在18岁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23岁成为哈佛大学博士
●1957年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这本在当时极具争议的书如今被公认为在美国军民关系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基于宗教传统把世界划分为数个相互对立的文明,并断言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引发有关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广泛争论
●2008年12月24日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的一家护理院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