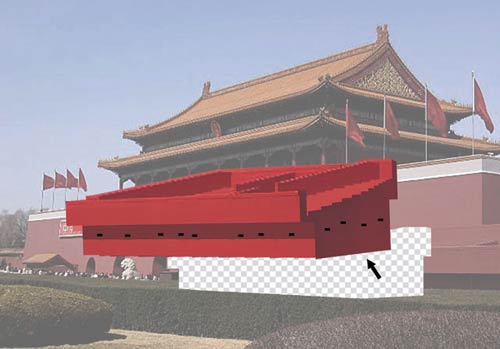
采访时间:2009年9月22日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
戴章伦:您如何去理解“国家遗产”这个提法?它与“文化遗产”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称其为是“国家遗产”?
朱青生:提出“国家遗产”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国家遗产”不是事实,不是真正实现的现实。它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社会文化传统问题在其形相的延续转换过程中的留下的痕迹,以及针对这种痕迹的判断、反应和再造。人们在对其观察、研究、陈述的过程中可以产生知识,同时,也因为要建造这样的知识、反省知识的构成,而进行艺术创造。这是探讨“国家遗产”问题意义之所在。
我比较认同此次展览的方法,这个方法瓦解了对Catherine David(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其展览反应了艺术中政治的当代性等问题)的质疑,即瓦解了对为什么要从艺术,而不是从新闻、记录的方式来关涉政治与社会的质疑。如果艺术可以直接表达对政治与社会的看法,就要让它表达出来,这是艺术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但是,责任感无论出自于何人,多不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至于“国家遗产”是怎样提出的,对其内涵的解释和引申,我想应该是由策展人来回答。展览的选题和内容都由OCAT来决定和运作,对于展览本身我并没有介入,北大方面主要承担研讨会的组织工作,根据已经成型的展览和展览呈现出的问题,跳出艺术界的局限,借助北大多学科平台和学术研究力量,邀请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各领域最为出色的部分学者集聚,从不同角度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国家政权的构成、显现及其文化传统,即中国人具有怎样的政治观念;新政权建立时,变更后的国家权力如何被表述,并且通过物质形态显现出来;这种显现方式背后的文化传统怎样。可以说,这次的研讨会,是OCAT联合北大视觉与图像中心的专家学术力量,推进跨学科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是中国当下人文科学领域高端学者一次聚合型学术会议。
那么展览做完之后为什么还需要讨论、展览和研讨会的关系、讨论本身的价值,是我下面会主要解释的问题,也是我站在研讨会主持人的立足点上,对你刚才问题的回答。
所谓“国家”,就是指政治权力,在这里,国家不是nationality(民族概念上的国家),而是political state(政治概念上的国家)。在中国,政治权力主要显现为中央集权的统治权力。中国对个人权力的认知无论从传统角度还是现实角度来看,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正因如此,“国家”的意味显得更为浓重。我曾经在国家画院做过一个演说,专门探讨为什么我们会有“国画”这样的概念,也就是探讨绘画中“国家”的概念。连文化中都不可避免的有“国”字头的影响,就说明了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此次“国家遗产”对于国家的讨论并不是一个虚假的问题,而是真实存在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再讲“遗产”问题。“遗产”当然可以说是一个被动的概念,即过去的如何遗留到今天,并且如何被运用为对后代有影响力的现状或将会在未来发生影响的因素。但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产”不仅是过去遗留给我们、被动接受的部分,还有我们今天保护并准备延续地流传给将来的部分。那么主动创造的部分是什么?在这个展览中就体现为几个艺术家的个案。艺术家通过形象,并非思考,而是印照的方式,或者说“情性”的方式,对直接遗留在我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中的形相物及审美关系做出进一步的揭示与呈现。这是必须需要艺术家作品的缘由。但是,在这个展览中,艺术家的起到的作用只是展览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构整个展览的方法,即展览本身就是对问题的回答。展览无论直接展示还是画册,都包含很多文献,这些文献在编排的过程中、在空间呈现的方式中,不是简单体现为陈述或者理论,而展览整体变成一种带有呈现性的艺术作品,使得展览本身也成为一件作品。这个展览其实包含了多层“作品”的含义:第一层,是艺术家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创作性的呈现,第二层是展览的制作人(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新词,叫“制展人”,而非“策展人”)所制造出的展览整体上形相的意义。第三,这个展览的catalogue(画册)邀请赵汀阳、巫鸿、汪晖这样的学者专门写文章,从各自研究的角度来对同一个方向的问题发表意见,将展览呈现为一个可阅读的理论文本,这一文本非常清晰。用逻辑、理性引发讨论,使形相再一次具有完全自由的被解释的可能性。如果说还有第四,那就是将在深圳举办的这次讨论会。
如上面所说,对“遗产”的讨论一方面是在探讨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了什么,另一方面是思考如何将现状留存给后人。这两方面总体体现的是一种将国家形象保存下来并继续呈现的行为,是中国人对待自己国家政治形象的仪式。这其中是否有传统的影响,以及传统能否延续,就是我们这次主要讨论的题目。
我认为我们对待“国家遗产”是有传统的,一方面是形相的继承,比如城墙、门以及背后的观念,即为什么要有都城、主干道、中轴线这样的概念。另一方面更为深刻,而今天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为何在关键时刻都保持着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譬如中国人从来不能接受国人去做汉奸,中国人没有选择做汉奸的自由。因为中国人认为,对于国家的忠诚是一个人的人格中间必要的部分,这也应该是文化遗产讨论的范畴。如果我们从这个根本问题上去追索这种观念的形成,就会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像西方知识分子,会抱有对文化传统继承和坚持的强烈信念。文化遗产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这个地方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会出现美协,会出现一群人为了权利、地位去打击和压抑不符合正统、不符合规范、不符合“国家利益”的东西。
这就是我组织这次的研讨会所想要讨论的问题,即我们要重新反省和梳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想把中国推向何方?他们是如何界定中国的语言、文化及传统的?又是如何在这个问题中慢慢建造出潜在的,不言而喻的核心价值。
中国人会为了公共利益,无论家族、集体、国家还是政治理念,牺牲少数人无所谓。比如我们很喜欢黄继光,而很讨厌投降、当俘虏的人。这样的理念中,个体的生命不能比政治意义、荣誉更重要——这是中国真正存在的精神遗产。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美国的“遗产”,即在推进国家创造力与公平理念的过程中,要保护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这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也在渗透到中国年轻知识分子身上,但是中国的国家遗产不是这样。
那中国的国家遗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我不知道我们邀请的各领域专家怎么看,这是我们研讨会最为看重的方面,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深究。在我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在社会生活中间强调人的“本分”,即合适的定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位置是社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位份”的概念特别清晰。譬如我们生活中常常要求一个人做事要“得体”,就是要求行为表现要符合所处位置的身份。“位份”的观念是中国人行为的主要约束。一如《红楼梦》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具有反传统精神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曾用这句话作为题字。“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人从来不是理性至上、规则至上、信仰至上,而是做人至上。“做人”就是得体,就是在你的“位份”上具有恰当的表现。
但这样的要求对个体的表达而言是不足够的,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和现实的处境有巨大的冲突。那就要求每个人在精神上不间断地自律和超越,而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不断寻求精神上的超越,而且中国人认为精神是有高下的,因而追求精神的高下、人品的高低的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评价即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位份”,由社会客观造成;二是“人品”,后者是可以通过精神上不断地努力来获得无限的提升,并以高低来判断,比如“清议”盛行,以及对“清誉”的看重。如《高僧传》序言中即讲,高僧之高,并非名声、地位,而是性质、品质之高。对于品质的评判就成为中国精神世界一个丰富的方面,就像中国艺术批评中“品评”具有不同的层次。
份位与人品的影响至今都可以看到,一方面看重每个人所处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又并非完全的媚俗,仍通过对“人品”的追求,保有不断努力的可能性。只是内在的评价和外在事实有巨大差距,造成了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文本,这其实就是国家遗产。“位份”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国家,而“遗产”中,包含了“位份”和“人品”。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价值观念的接受者,中国当代艺术永远不可能做成美国艺术。这是“遗产”意义深刻之所在。
“遗产”概念到今天也还在用,就算当代艺术中的“骨鲠之士”,反传统的艺术家,也都很会做人,这也是一种精神遗产的显现。有人说中国艺术精神是道家的,社会行为是儒家的,不一定准确,但从一个角度印证了我对遗产本质(“位份”和“人品”)的分析,即行为上要求得体规范与精神上追求自由两方面矛盾的统一。 |